热点资讯
- 自拍偷拍]藝校兩女生自慰裸聊視頻 王晶亲爆料邱淑贞夙昔拍三级片全裸,坚握不漏隐痛部位。|马|作者|性感女神|赤裸羔羊|电
- 【ADVSR-021】クライマックスダイジェスト 姦鬼 ’10 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
- 调教学生妹 官宣!旗头辜海燕、王人勇凯
- twitter 拳交 双胞胎姐妹花: 因林徽因而钟爱建筑系
- 自拍偷拍 telegram 黄药师
- T先生系 被问爆!在都江堰风景反反复复去吃的5家“漂亮饭”!|老街|图据|都江堰市|低价好意思食
- 裸舞 女东谈主最受不了的作念爱妙技
- T先生系 审核评估须知应会第10讲“两性一度”的内涵
- 文爱 聊天 北航执行学校中学部高三年事举行成东谈主庆典暨百日主题栽种举止
- 【ADVR-480】発情マゾ愛奴 可编程拼插机器东说念主“KOOV™”发布
周处除三害 麻豆 【中台世界】─ 《佛說四十二章經》──第二十一章好名無益【名聲喪本】
- 发布日期:2025-04-22 11:08 点击次数: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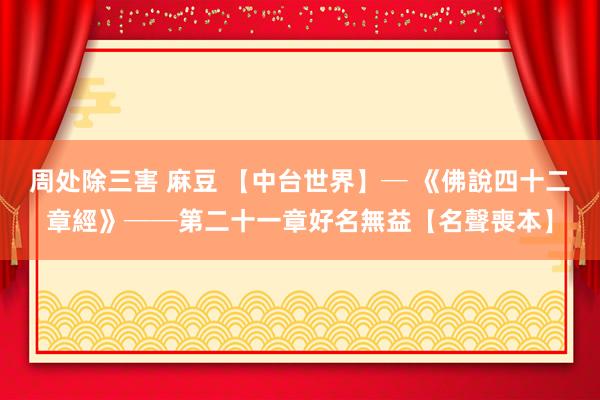
《佛說四十二章經》──第二十一章 好名無益【名聲喪本】 (一) 周处除三害 麻豆
佛言:「东说念主隨情欲求於聲名,聲名顯著,身已故矣。貪世常名而不學说念,枉功勞形。比喻燒香,雖东说念主聞香,香之燼矣,危身之火而在其後。」
這一章「好名無益」,是佛陀教导我們不要貪求名聲。「好」等于喜好,「名」等于聲名、名利,追求名利,實在沒有好處。一般东说念主在沒知名的時候,都喜歡打知名度;比及信得过有了名,才知说念名是祸首禍首,所謂「樹大招風」,為我方帶來好多麻煩。中國有一句俗話:「东说念主怕出名,豬怕肥。」豬肥了,命就沒了;同樣地,东说念主出名以後,也會际遇種種風險。
一般东说念主都喜歡知名,拼命地追求名聲。所謂「大名鼎鼎」,假使名氣很大,無論走到哪裡,全球都認得,我方就覺得很振奋、很威風。舉例來說,現在的選舉,候選东说念主沒有一點名氣,就很難選得上,是以為了打知名度,常常就虛張聲勢,膨脹我方,也等于所謂的「造勢」,認為有了名,利就隨之而來。
往日山上有一位居士,還沒有學佛往日,曾經參加選舉,當了政府官員。學佛之後,雖然知说念要把名利看破,但沒有辦法信得过看破,仅仅懂得一點意旨辛苦。有一天他告訴師父:「佛法真好!救了我一命。」我問:「佛法怎麼救你一條命呢?」他說:「我往日不懂佛法,只知说念膨脹我方,處處都要顯現我方的精熟來打知名度。比如開會時,我就要想個顺次來凸顯我方,找個事情來罵一場;學佛以後,才知说念這是罪過,造了好多口業。」
又說:「當了官員,有的事沒有辦法推辭;举例,經常會被選民請去撐場面,有些东说念主娶媳婦、生孩子,辦宴席的時候要去露個面;有些东说念主家裡長輩作念壽或有东说念主往生,也要去照個面……種種婚喪喜慶、情面世故,從早到晚許多場,若不去怕會得罪东说念主,是以非去不可,去了,聽到掌聲、讚歎,就感到很受用!但是這種場合實在太多,是以常常只去幾分鐘就走了。」
「有一次,有一戶东说念主家娶媳婦,我和祕書一王人去,卻穿著黑西裝、打著黑領帶,對他們說:『請節哀!』祕書趕快在旁邊提醒:『东说念主家是討媳婦呀!』為什麼會這樣呢?等于失去覺性,被外面的名利意境操纵,迷失自我,心裡迷混沌糊的,分不了了因緣,才會如斯。現在學佛了,才找回信得过的我方。」
一般东说念主沒知名,就拼命去追求;有了名,又產生種種罪過。由此可知,「好名」無益。罪過,是來自於貪求名聲的心;假使有了名而不貪著,等于信得过的菩薩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當中,觀音菩薩以三十二應身隨機度眾,示現天子、宰相、總統、院長等應身來濟世。為什麼呢?因為东说念主微言輕,假使沒知名位,就沒有辦法作念大事。世間法都是相對的,運用得好,等于一種功德;用得不好,就會帶來煩惱,以至造惡業。是以,佛法要應機施教,運用種種便捷來弘揚佛法;假使統統都不要,就太消極、太悲觀了。
任何事情都有一體兩面。有了名而不貪愛,又知说念學佛、作念功德,藉由這些名位、權勢來弘揚佛法、普度眾生,就像觀世音菩薩一樣,「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這等于信得过的菩薩行。违暗自,有了名,卻不知说念经法的意旨、不知说念運用名位來種善因,反而特別好名、貪名,膨脹我方,這樣就一點好處都沒有。
佛言:「东说念主隨情欲求於聲名,聲名顯著,身已故矣。」「佛」,等于指釋迦牟尼佛;「言」,等于告訴大眾。「东说念主隨情欲求於聲名」,东说念主為什麼會貪名呢?等于隨著「情」、「欲」這兩個意境,因為东说念主有七情、五欲;假使沒有七情、五欲的煩惱、執著,聲名也毫無用處。
何謂七情、五欲?「情」,是神气的一種變化。眾生都多情識,以佛法來說,多情,等于眾营业境。眾生屬於迷情,心中有種種想愛;菩薩屬於覺多情,雖然是多情,但是覺悟的多情。
眾生有親情、愛情、友情……由於有這些情愛、空想,是以才求於聲名,但愿別东说念主细目我方、但愿我方有所竖立,這些都屬於情和欲。儒家也講情,《禮記》云:「何謂情面?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喜」等于歡喜,「怒」等于發脾氣,「哀」等于悲伤,「懼」是恐懼,「愛」等于情愛、色愛,「惡」等于討厭,「欲」等于但愿。一個东说念主的神气變化,不过乎這七種,稱為七情。心當中有了這些執著,就屬於眾营业境。
「欲」等于但愿,共有五種,稱為「五欲」,也等于對於色、聲、香、味、觸五塵,產生色、聲、香、味、觸五欲。有了這五欲、七情,隨著根、塵、識產生貪著,眾营业境現前,就有了死活。
「求於聲名」,「聲」等于好的聲音,如掌聲、讚歎等;「名」等于「名氣」。「聲名顯著」意即聲名遠播四方。「身已故矣」,身體已經壞掉、死掉了。一輩子都在追求名利周处除三害 麻豆,名利雖然竖立了,身體也一火故了。這等于告訴我們,對名聲要看破、放下。
「貪世常名而不學说念,枉功勞形。」「貪世常名而不學说念」,只知说念追求名利,而不知说念修说念,谢世間上來講,「只見其利,不見其義」,等于沒有说念德。有了名還不滿足,進一步還貪名;貪了名,又不知说念作功德、不知说念修行,就「枉功勞形」,白費功夫。假使貪名而不修说念,將來一定會墮入惡说念;相對地,不貪著聲名,而是藉由聲名來作種種佛事,就不會「枉功勞形」。
「比喻燒香,雖东说念主聞香,香之燼矣,危身之火而在其後。」如若名义上有好的名聲,但實際上並沒有好的德行,等于所謂「欺世盜名」,將來業障現前,一定會受惡報。「比喻燒香」,如同燒香一樣,香煙瀰漫,东说念主东说念主都聞赢得香味。有些东说念主有了名聲,到處逢場作戲、虛應故事,製造一些假相,藉此獲得他东说念主细目。「雖东说念主聞香,香之燼矣」,就如同燒香,聞到香味時,香已經燃盡了。現在全球雖然聽聞你的名聲,就随机燒香聞到一點香味;比及香燒完结,這一世若沒有修到一點功德,最後命也沒有了,就只可隨業流轉。「危身之火而在其後」,將來業果現前、東窗事發,誰也替代不了,假使觸违规律,不但這一世要入狱,未來還要受業果的報應,由此可知,好名是無益的。
东说念主為什麼要追求聲名?因為情欲的緣故,假使沒多情欲,当然而然贤达現前,任何事情都看得很了了。披缁修行,食衣住行都是十方善信供養,假使不知说念勤恳辦说念,反而在這裡打休想,尤其是欲愛、色愛的煩惱,不知说念返照,通不過這一關,就會退失菩提心。
情欲进犯易看破,名聲也进犯易看破,是以俗話說:「酒色財氣四堵牆,當中埋的是英良;若能跳出牆門外,此是長生不老方。」情欲當中最嚴重的等于男女之欲,這是死活的根柢。無論是佛法,或是儒家、说念家,乃至其他宗教,都提到男女欲愛的過患。
欲愛猶如一把火,欲愛之心一王人,欲火燒身,心當中就得不到耐心,容易失去寡言。在醫學來講,男女的愛欲太過熾盛,身體會出舛错。男性貪著女性,唯有一動念,欲火馬上就燒起來,身上坐窝發熱、發燒。如若繼續打休想,欲火會一直燒到全身,以至燒到頭腦,一朝失去了寡言,什麼事情都作念得出來,現在有好多亂倫的社會案件,都是放縱情欲的結果。
《楞嚴經》云:「菩薩見欲,如避火坑。」假使心中有七情、五欲,就得不到耐心。所謂「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這都是因為情欲作祟,假使不知说念勤恳、返照,修行就进犯易竖立。《楞嚴經》云:「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可得。」就如同想把沙煮成飯,是錯亂因果。是以,要想成说念,最初要對治情欲。
显明情欲的過患,就能轉識成智;若不解白,就會喪身失命。儒家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等于我們的心水。心水清淨了,等于菩提心;愛欲不除,心水就不清淨。是以,如若能夠檢討、返照、克制情欲,水就能載舟,就能超凡入聖,從煩惱的此岸到達涅槃的此岸。我們在這個社會修習菩薩行,當中的分寸要拿持得很穩。 (二)
《中和》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未發」,等于沒多情、沒有欲,一念不生,中说念才會現前。儒家又說:「好处復禮,寰球歸仁焉。」「罔念作狂,克念作聖。」「克念」,等于能夠返照、克制我方的情念、欲愛。唯有能在這個处所下功夫,就能夠超凡入聖。
佛法中,无论任何派系,都把情欲視為一個關口。淨土宗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禪宗則說:「有一些些,還有一些些。」什麼趣味呢?唯有還有一些些情欲,將來就還有一些些死活,還要來受報。修行东说念主要知说念從這裡修,這個处所不可開便捷。這念心一動,等于死活的根柢。中國有一句俗話:「紅羅帳內真地獄,鴛鴦枕上活刀山。」等于指情欲的禍害。
显明這些意旨,就了解修行是进犯易的事情。修行东说念主發了菩提心、發了大願、想要得解脫,如何才气解脫?不是死荒谬解脫,也不是靠佛菩薩接引得解脫,唯多情欲沒有轉過來,無論到什麼处所都是五濁惡世,到什麼处所都是黑暗、苦惱。是以,必須從這念心下手,心清淨了,佛土就清淨。心怎麼樣才气清淨?等于要克制我方的情欲。
佛法有漸修、頓悟的法門,無論是哪一種法門,都是幫助我們到達涅槃此岸。要克制我方的情欲,不错修九想觀來對治,這是漸修法門;以頓悟法門來說,所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悟到中说念實相,一念不生,等于解脫。無論修任何法門,但愿修行有所竖立,等于要斷除情欲。
情愛是死活的根柢,唯有有了情欲,煩惱就隨之而來,失去了贤达、失去了寡言、失去了良知,這念心水就變成混濁的水。有些东说念主不了解這個意旨,認為「食色,性也」,貪愛食色,是东说念主的天性;事實上,貪愛食色,是眾素性,而不是聖性、佛性。是以,要想轉識成智,就要從這念心上來轉。
無論世間法或出世間法,一切事物都離不開因緣果報。現在的东说念主不了解這些意旨,家裡有内助,還在外面金屋藏嬌,導致家庭不仁爱,事業也走下坡,作念什麼都不順利。這樣一來,求佛,佛也不應;求菩薩,菩薩也不靈。什麼原因呢?因為放縱情欲會減損我們的福德因緣,心當中失去了功德法財。违暗自,能夠克制情欲,福德因緣馬上就能增長。
宋朝有一位儒生,名叫林登雲,家住江南,有一天搭船到京城考進士。途經吳淞江,因天色已暗,船伕就把船靠岸在河邊的樓房下。更阑裡,河邊的樓房忽然动怒,好多东说念主都被燒死了,有一個婦东说念主從樓上跳下來逃生。時值十二月,天氣阴寒,林生看婦东说念主衣著單薄,並沒有欲念薰心、趁东说念主之危,而是趕快請這位婦东说念主到船上來避寒,並且把我方的皮袍脫下來給她穿,讓她遮羞、取暖。林恐怕船伕對婦东说念主見色起淫而有所骚扰,是以徹夜挑燈讀書,不敢寝息。比及天亮,把婦东说念主護奉上岸後,才揚帆離去。
林生進京考進士,由於他的著述並不是很好,考官看他的著述也不夠水準,就把考卷拿到旁邊去了。到了晚上,考官作了一個夢,夢到關公在這篇著述上批:「裸體婦,狐裘裹,秉燭達旦爾與我。」考官醒來後心想:「這個东说念主可能是積了什麼福德。」第二天就召他詢問,來京的路上是不是曾經發生什麼事。林生答说念:「沒有。」考官就說:「我本來是不想錄取你的,但是昨晚夢到關公批了這幾句話,随机在教导我應該錄取你。你必定是積了陰德,才气赢得關聖帝君親賜功名。」林生一趟想,就把這段經過告訴了考官,考官就錄取他了。
儒家也講好多節制欲念的意旨,佛法是修出世間的解脫法門,更應該了解男女的欲愛、色愛,為死活的根柢。是以,必須經常返照這念心,冉冉地心就能夠平靜下來。心平靜、澄淨了,当然就能赢得解脫。
佛法有大乘、小乘。以小乘來說,修说念之东说念主必須離開家庭、離開社會,離開一切名利,再去修行求證真空,稱為「離俗求真」。大乘則是「即俗即真」,名不一定是壞事,有了名聲而不貪著,藉此因緣來弘揚佛法、護持三寶,作種種佛事。所謂「宴坐水月说念場,大作夢中佛事」、「巧把塵勞為佛事」,等于信得过的菩薩行。
現在的社會和過去不一樣,為了弘揚佛法、普度眾生、建設说念場,使佛法廣傳,就要藉由種種因緣來作一些正面的宣傳,這樣一來,名就不是罪過。是以,一切都是這念心的運用,有了名而不貪著,藉此因緣廣作佛事,等于信得过的菩薩行。有些东说念主不了解這個意旨,認為既然名利是一種罪過,乾脆侧目东说念主群,不願意承擔弘法的重擔,認為這樣才是不好名利,假使每個东说念主都是這種宗旨,佛法就滅掉了!
師父披缁之前,看了好多小冊子及論著,認為不作方丈、不作當家、不建说念場,才是修行东说念主。是以披缁以後,在大覺寺住了兩年,就到外面去行腳。行腳途中,也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現象。有一天晚上,去一個说念場掛單,對方說沒有处所可供掛單。我說:「沒有關係,有個处所不错坐一坐就夠了。」於是他們就把師父帶到一個处所,說:「這处所好不好?」一看,是一個很大的籠子。我說:「這是什麼籠子?這麼大!」他們說:「這是養雞的籠子,今天把雞都賣了,籠子恰恰空著,你不错到裡面去坐」。
經過這件事情,才知说念往日的觀念是錯誤的。現在的说念場好多,當中也有邪知邪見的,假使不建说念場、不作方丈、不作當家,佛法可能就被這些邪知邪見給毀了。是以觀念要調整過來,不是為了我方的竖立而來辦说念場、作方丈、收门徒,而是為了佛法的命脈。
有好多論著,內容並不是佛知佛見,仅仅作家我方的宗旨,是以不一定正確。在過去,不需要披缁眾來建说念場,十足由在家居士供養,以至有國家君王的護持,但現在的因緣與過去不同,必須調整觀念來因應時代的改變。我們現在不但要建说念場,况兼要建更大的说念場給更多东说念主來修行、勤恳;不但要收门徒,况兼要收更多想要修行的东说念主……标的等于使每一個东说念主都能夠深切佛法、了解佛法;显明這些意旨,就知说念在這個世界上,通盘事物都是一體兩面的。
是以,對於名、利,不是不要,而是不貪。想想看,如若我們沒有錢,要住在什麼处所?吃什麼?穿什麼?在這個時代隨順因緣運用名利,為大眾、為说念場、為佛法作念更多的事,不但沒有罪過,還有不可想議的功德。
大眾都很有说念心,想打坐、聽經聞法,這是善事情,但也有好多东说念主不想擔任職務,認為這是好名圖利;以至有东说念主告訴師父:「師父!东说念主家稱您為禪師,您應該去打坐,不要建設说念場了。」這些觀念都是錯誤的,由於知見沒有圓融所產生的執著,如若全球都如斯,誰來弘法辦说念,眾生如何能聽聞佛法?
佛經中提到,披缁比丘、比丘尼要竖立三件事情:第一,修福報,也等于修善法;第二,博學多聞;第三,修習禪定。显明這些意旨,不論作念任何事情,都能夠很圓融、很闲静。建設说念場、弘揚佛法,是荷擔如來家業,是披缁东说念主的分内事。有因緣,就一定要去作念,仅仅不貪著竖立,這是最迫切的。是以,知見要圓融,祖師云:「巧把塵勞為佛事。」有了名利,藉著聲名的因緣,竖建功德、竖立说念業、竖立佛事,這等于菩薩行。
單元首頁
周处除三害 麻豆
